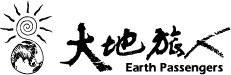撰文 / 方雅慧(2011創意的轉型社區營造引導技能工作坊學員)
此次參加大地旅人於台東都蘭部落所舉辦為期五天的工作坊,很慶幸自己選擇了在這個時間點參與這個活動,也在工作坊中結識許多不同領域的夥伴。成員的異質性與個體的動能與熱情,依著工作坊的進展,逐漸深厚彼此的看見,營造出一種促進社群情誼的社會空間。對我個人來說,時機的巧妙回應了自己的困頓,與自己自在地置身在團體當中,感受到被支持的溫度,是我從都蘭回程中隨行帶著的珍貴禮物。
身為教育工作者,我重視自身與他人的生命發展。當教學發生在同時進行社區與公共事務行動,我經歷了如Palmer筆下所說的內在視界:…置身於個人與公共事務的交集處,在接踵而來的各種關係之間折衝樽俎,遊刃有餘,就像試圖徒步穿越車水馬龍的高速公路一般。這樣的交戰狀態,在每一個行動中上演,動態的現場,既是不斷地試探自己的專業判斷與行動,也試煉著作為自己教育工作者的心。雖然自己多年投注在社區營造場域,也擔任大專院校「社區工作」、「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課程授課老師有近四年的歷程,在我自己進行個人的博士論文時,我的個人探問,是從嘗試探索自己在社區工作歷程中最核心的課題出發,專業工作者的修煉為何,何謂價值與信念。這樣的提問,成為我在社區工作現場,乃至在後設的反思整理時的核心的議題。尤其是自己於98年初取得博士後,當時的我為自己設立了一個目標,希望能在未來的研究與行動中,持續探索女性社區工作者的專業反思,藉由探究社區工作者自身實踐歷程的外觀,以及自己實際投入陪伴社區工作者的實踐路徑,作為自己探索工作者認同的題引,以滿足理解自己如何面向世界的渴望與好奇。

在98年至今,我刻意讓自己擺放在「孵育」的狀態,用一種隱喻的說法,就是「把自己再度放回保溫箱,繼續孵化在論文中尚待深究的課題」。我讓自己的生命織進著「社區、教育、社區工作」面向世界的端點,透過敘說、對話與各種療育性的活動,促成參與者與我的互相看見,從「進入他人的生命與經驗」中,從中騰出足以讓自己能夠參看自己的位置。這種把自己成為「媒介」與「工具」的方式,在年初自己面對至親辭世之後,因為哀慟所牽動的身心狀態,我感覺到自己雖然仍在「十字路口」,但彷彿失去了前進的目標:在十字路口徘徊,陷入「失去存在」的意義感中。在感覺到自己脆弱的情感狀態,以及對於「轉型」的殷盼,在這個時間的當下,參與這個工作坊對我有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提供了關於尋覓自身生命意義與確信的歷程。
這一切須感謝工作坊帶領人Robyn創造了一個不評價、鼓勵探索,安全且尊重的社會空間,它是由許多細膩的社群經營、審慎考量異質經驗所創造出具包容性的儀式構成。工作坊的進行過程,雖然臚列了社區工作中關於技術、認知與情意等面向,以及理解社區基本面向的工具引介,Robyn顯然在工作坊中更重視在態度與價值觀的「轉型」(transformation)工作,以深層生態學的視野,在工作坊課程的開始便直搗探究社區工作者的世界觀,從第一天晚上的「轉型工作坊」到第三天的眾生議會,以團體共同體驗群際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連結感,解構工作者心中自然與人斷裂的社區工作認知。Robyn把社區工作的視野,從辨識解離的社區內部的人群與自然狀態,推移到植基於人對自然須相互共生的倫理實踐所發展出具民主包容性、強調正義的參與式作為。如同補綴者的身手,將在生活世界中被斷裂化、切割分化的關係與脈絡梳理,並提供一個具公共性的參與,以盡可能網羅所有利益關係人的過程,涵容所有人的想望與期待。我想,Robyn心目中的社區工作者的樣子,應該是一個樂於在人群當中,和一群人工作完成「百納被」的。其中的意義的創造,在縫製百納被的過程,也在大家共同織就成的作品本身(如Edwards提到「實踐是習得民主技能的最佳方式(2)」)。
回想,這樣的社區參與的精神並非是新興的派別,但這盡乎是社區工作的普世精神,卻少見諸於台灣目前眾多標榜「社區參與」與「社區營造」的案例經驗當中。檢視國內案例的普遍狀態,可以解釋的理由,除了可從社區組織的組織發展狀態與對應國家的互動關係進一步分析之外,此外在社區工作部份偏重於強調實務技術,而忽略工作者信念與專業倫理發展有關(在不強調專業倫理的狀態之下,社區工作容易國家政策意志貫徹、專業者未能反思專業權威而再製了知識和權力的不平等的場域)。Robyn所強調的與堅持的,是呼籲回到初心,提出一種從探尋根本解的社區工作流程,而非落入見林不見樹的症狀解。
在社區工作中要堅守根本的原則,可貴之處在需要保持著某全觀的和高度反思的心性。從工作坊過程中我的體會,Robyn的做法是從靈性面切入,喚起個我的「大我」,或者是Abalos(1998)所謂的「神聖性」。借助團體動力與儀式過程,我們都能夠在群體當中確信自己不可或缺的價值,並從多感官的互動過程中,召喚出上位的普世價值作為共同願景,由成員重新定調自己的個我行動。於是「共享」、「承擔」、「委身」與「承諾」來自於成員自我許諾的選擇,也來自成員自我願意面對風險與犧牲。由此可以初步斷定,工作者持續地從靈性經驗中確信工作價值與自我認同,對於深化工作實踐的重要性,應較專業技術更被置放在核心的工作者養成的位置。這三年來我嘗試從「社群共學」的概念,在社大與屏東的社區組織,發展工作者與社大教師培力的系統性過程,也在嘗試回到「看見生命」的位置,作為共同出發探索「如何面向世界」的起點。我們初步實踐的發現:在安全與尊重的空間中,我們能夠走出因為斷裂而疏離的歧見與對立,朝向相互支撐也彼此相互提醒,跳開個人主義式思考框架,逐步去厚實以人際為基礎的知識。這群我關係的改變,將促成大家願意委身於自己所信奉的理念價值,透過集體的「踐行」重新建構社區工作場域中人與環境的基進關係。That’s IT!我驚喜「社群共學」與這工作坊精神間的「相映」。
在工作坊中能夠以學習者的身份投入,對我來說是件幸福與感恩的事情。之所以幸福,在於跳脫有經驗社區工作者的位置,進行歸零學習(unlearning)是不容易的過程(我認為歸零學習是拆解框架與專業主義的重要手段,也與轉化攸關)。有機會卸下習慣的社會角色,讓自己學習成為學生重新學習,是深具意義的一步。我確實覺得,浸染在與工作坊成員共在的學習關係中,真的有種微醺的幸福感。
之所以感恩,是此刻自己走在「絕望」(或者對應著「絕望」盡頭處的「新生」)的邊界(這與我一直是給人「旺盛到好動、亢奮」的獅子座外在狀態很不協調),曾經多次在工作坊中因覺察自己的內在狀態而留淚。在工作坊中五天的時光,讓我有機會沉潛面對自己,整理我和過世的奶奶間連結關係(bond),以及自己仍處在不放下的否認狀態。工作坊的氛圍讓我無須掩飾脆弱,這使我有機會把自己置放在「絕望」的狀態之中(而非慣性地跳開),細細經驗「絕望」背後給我的諸多教導:
「絕望」不只有「絕望」的情感本身,它蘊含著流動與再創造的潛力。「絕望」帶來的情感狀態,直探生命底蘊,它的豐饒一如它具毀滅性的本質,深具「學習性」與「社會性」的意義。記得某位老師曾經提到,今年接待John Seed來訪時,John特別跟他分享了關於「培力與絕望」(empowerment and despair)的概念(有趣的是,Erickson也在其提出的「人生心理社會階段理論」中指出「絕望」與「統整」的關聯性)。就像在基進成人教育運動中,會出現「憤怒」(anger/rage)的字眼,代表著對不公義狀態的義憤填膺,也宣示了以肉身行動來創造「希望」的企求。我想,體會情感經驗的層次與質地,或許可以更立體地看見不同情感狀態中的生命風景。面對「絕望」,走在這路上,通過它,我才能朝向「統整」。凝視這些鑿刻在個體身上的經驗,或許才能同理到對方所體會的意義感,而走向相遇。
告別都蘭的隔周,我受邀針對屏東縣的社區與社福機構工作者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婦女跨領域行動實踐」,並於專講後協助帶領小組進行分享討論。我試著修正「犀利人妻->走進社區->社會參與」(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單向關係,邀請與會者回到自身,檢視自己人生中重要的關鍵時刻(童年經驗、求學畢業、成為父母親等),並肯認自己的性別角色與生命經驗,進而建構自己「面向世界」與「向內探求」無限度交織的行動軌跡。
何謂「跨領域」?
「跨」作為一種拒絕「被歸類」的抵抗行動,意識自己所面臨的界限處境(對於「置在邊緣」的自知之明,成為後進行動實踐的土壤)。女性工作者的「跨領域」:家庭vs.公共空間、母職vs.做自己、工作職責vs.工作者認同、個人vs.社群生活….跨族裔、跨階級….
何謂「行動實踐」?
凝視自身,面對「被卡住」的狀態(界限行動),以一種願意承擔風險的承諾創造自己生命的變遷,於是,面對邊界/界限,為「追求自由」的叩門。
我也帶著工作坊中友人送給我的一句箴言-世上霧中黑暗的烽火(brillance),與參與者分享與相互期許,成為同行路上照亮彼此的光。
面向世界,是「向內探求」的回家之路。我仍在十字路口,帶著自己的人生功課,傾聽自己的心跳,感應心所指引的下一個方向。
(1)「覺察」一字的內涵,將借用Ericson的「高度的知曉」(heightened awareness)所提出的註解。即對於「靈性的個性」的「我」,確認是空間及時間上的中心(而非位居邊緣)、是明顯光亮(而非被遮掩)、是活躍被啟動了的(而非被動的)、是繼續性(而非分散的)、是包容性的(而非孤離或排他的)、有著安全界限的(而非易被侵犯或逃避的)、被選的(而非被忽略的)(Erikson , Erikson & Kivnick著,周伶利譯,2006:70-71)。
(2)Edwards, Michael(2009),p.89。
(3)Abalos(1998)提到:「轉化的歷程都是從個人角度開始的,但我們每個人都有四個面向:個人、政治、歷史與神聖性。要去除我們個人生活和社會中的惡靈,我們必須釋放我們的神性。」(Abalos認為重新宣稱「面孔」是個人的也是文化的歷程。)